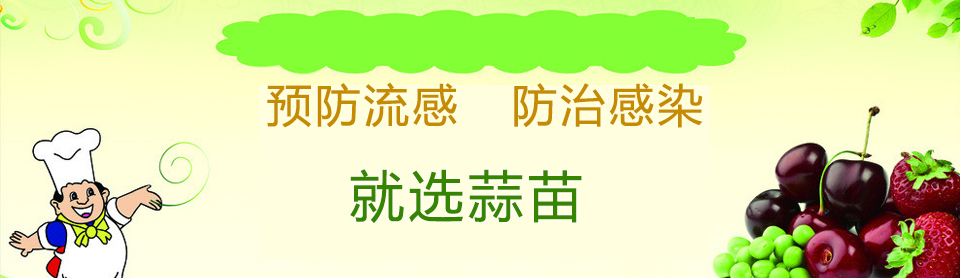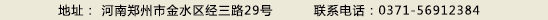诗中节令田园绿遍山原白满川明月几时
今天是太空与您相伴的
中国人对田园有着天生的好感。
我的父母是从农村考到城市里的一代,祖父母那一辈人,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我生长在城里,回乡下外婆家是我最期待的事情,一到了那儿,就总也不想走。
那个小村子最好的时候是初夏。初夏的清晨听得到布谷鸟的叫声,这鸟儿叫得很有趣,一声鸣叫里长短错落,抑扬顿挫,我总是想听清楚它的歌儿,却无论如何也分辨不出唱得究竟是个什么腔调,就这样一不留神,天就大亮了。
炊烟升起又消散,隔壁的舅舅家,大门吱扭一声响,我知道他们去“下地”了。
从我记事起,老家的地里种的一直是大蒜。蒜卖得上好价钱,却最费功夫,除了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收获,种大蒜还多了一件事,就是“堤蒜薹”。“堤”字到底怎么写,我不知道,只知道村里人人都这么说。
蒜薹是蒜的花茎,要在它刚刚露出头来的时候就尽抽出来,如果任由其生长,蒜头是长不成的。所以“堤蒜薹”是立夏前后整个村庄里最重要的事,往往是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,连上学的孩子,都躲不了这个清闲。
我跟着表姐去看“堤蒜薹”,她手里拿一根木棍,木棍一头带一根铁钉,往蒜苗上笔直地插过去,芯子断了(这时候的蒜苗很粗壮,不用担心会整根折断),再从上面快速地一抽,长长的一根蒜苔就在手里了。我想也许这个“堤”字,就和蒜薹抽出时的“滴溜”一声有关吧。这个动作我总学不会,蒜薹到了我手里,总是可怜巴巴的一小截,引得大家捧腹。
城市的超市里,蒜薹是一样价格不低的蔬菜,但这里的蒜薹就如同麦收时的麦草一般,田野里、庭院里,无处不在。抽出的蒜薹,人手充足的人家,绑成捆,拉去村口卖掉,人手少的,就随手丢在地里,任它“化作春泥”了。
不用说,这个季节各家各户的餐桌上,蒜薹是绝对的主角。蒜薹炒肉丝、炒鸡蛋、烧鱼、煮汤,简直无所不能,以至于我至今依然不愿意买超市里的蒜薹,总觉得在老家的田野里,还躺着成捆的蒜薹在等着我。
当然也不止有蒜薹。外婆的小院子里,开了半亩大的一片小菜园,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韭菜、西红柿、小白菜,各种菜蔬密密地种了个满当当。初夏时小白菜正茁壮,韭菜也才割到第二茬,做饺子馅正合适,其他的则还是绿油油的叶子,不通庄稼事的人,一眼看去也分不出是什么。
小时候外婆在偶尔来我家,住不到一旬,就一定要回去,说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园。那时候我不理解,心想这么一点蔬菜,有什么舍不得的呢?直到多年后,我读到宋代翁卷的一首《乡村四月》,诗中写道:
绿遍山原白满川,子规声里雨如烟。
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
我才恍然,这不就是外婆舍不得的那片原野,离不开的初夏田园吗?
但长大后的我,鲜少有时间再去外婆的田园里过一个初夏了。一年复一年,那份对田园的怀念,在心底越来越强烈。终于,我在立夏前休了假,回了趟老家。
外婆已经年过耄耋,早已不是儿时记忆里爽利的样子,院里的小菜园反而更大了些,靠里的一半,舅舅给种上了大蒜,外面留了两畦韭菜,和几棵用来留种的菠菜。正是“堤蒜薹”的季节,随表哥在城里生活的舅妈也回来帮忙了,还带回了她六岁的小孙子。她弯腰做着手里的活,孩子跟在她身边,在田埂摘荠菜花,祖孙俩一边向前缓缓地走,一边聊着天:
“奶奶,大蒜什么时候种呀?”
“大蒜秋分种。”
“奶奶,那大蒜什么时候收呀?”
“大蒜小满收。”
于是突然觉得,这段对话竟像在写诗一样。
《诗经七月》有:
“四月秀葽,五月鸣蜩。八月其获,十月陨萚。”
与此神似。原来田家的生活与诗竟是同样的美丽。
我帮着外婆“堤”小园里新抽的蒜薹,动作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笨拙,惹得外婆笑了起来。看着过膝的蒜苗,我想,这土地可真好,只要你种上一粒蒜子,然后浇灌它,照顾它,它就会还给你这么茁壮碧绿的一颗蒜苗,还有一头白胖胖的新蒜。靠着这土地,外婆养大了我母亲兄妹三人,舅舅又养大了表哥表姐们,这是多么质朴的事实,却又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。
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。
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几千年的文明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生生不息,几代人就在这样的土地上养活着自己和子孙。这本身,就是一首最动人的诗。
来源
我们的太空(ID:ourspace)
原标题:《田园:绿遍山原白满川『明月几时有』(61)》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sh-chenfa.com/smxg/2115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