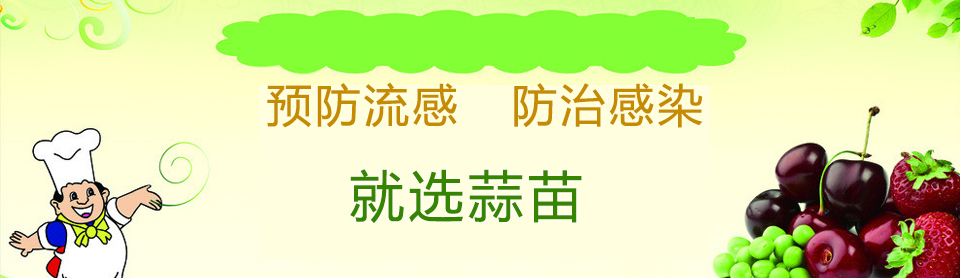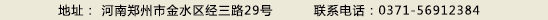崞县风物志任晋渝冬令草木状
请戳:享道商城
冬令草木状
任晋渝
我一直以为每株花木里都住着一位仙子。
一枚:仙客来
随母亲回祖屋,看到窗台上放着许多泥盆。里边栽着吊金钟、洋绣球,还有仙客来。好多仙客来,大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发紫的,一簇簇,把窗台占得满满。
进来个隔壁。乡里管邻居都叫隔壁(jiēbiě)儿,肯定是看到妹妹停在胡同里的车,过来看这家什稀罕戚人来了。攀谈起来,就说,“你看你奶奶的花,多喜气。”她发音不大标准,我听“喜”就是个“仙”。母亲是最喜欢花的,自然接话,“怎么种的。”站在地上的奶奶随口一笑,“我也不知道,就那么稀里糊涂种,有时候,说养的麻烦扔了哇,可你公公(我爷)就不让,说好歹是条命。”把话题岔开,晓得我们定是坐会儿便走的。忙乱着去抓小米、糕面、馍馍。
地方上产糜谷。小米熬稀饭,色金黄,像铺层油。糜子呢,可以做糕。自己蒸了自己炸。这边乡里的糕,随这边人的性子,好“捏抓”,老实、柔和。越放越软。不像旁处的,高傲,犟。一顿下来,第二顿,就成了死硬派。母亲晓得我爱吃,便让拿上。其实,我并不会做。以前,总是父亲做。父亲不在后,母亲虽也动手。但许多亲戚都怕躲着,就很少回祖屋,自然没得糕面来处。
因为要过年,馍馍是该带的。这边有个俗,家里一个人,一个“马蹄蹄”(一种面食)。由长辈赠与。我有回推脱,奶奶说:“怎么,嫌我们脏?”自那以后,再没推脱。《常礼举要讲记二》讲:“长者赐,不敢辞。”大约就有这一层意味。
找到父亲后,母亲嘱咐我们,“你爷奶老了,能眊的次数不多了。有时间,一定回去眊眊。”她自己定的时候,每年正月初四,都得去。我们便将妻携子或将夫携女,一个不落地回去。又一回,仍是母亲,说,“你爷现在地不种了,没别的收入,你们该孝敬,就算给能给多少年?”打那之后,我和妹妹都有了给钱的例。我在太原,少回故乡。逢节,母亲都会自己去。一般都妹妹开车。有回妹妹病了,她居然在亲戚里问回村的车和下来的车,什么时间点,在哪里坐。
我知道母亲其实是很喜欢仙客来的。回到县城后,她有许多次提及奶奶的花开得多好。但她从来没问奶奶要过。就好像许多年前,她从来没向老人们要过旁的东西。不过,后来,她还是有了一株自己的仙客来。
母亲在县前进街租一节柜台,卖副食。那年国庆,前进街上摆了许多花木,有菊花、鸡冠花,也有仙客来。散场后,许多花木被遗弃在道旁,不及收拾。一些路人纷纷去捡拾。母亲下班路过,也去。回来,家里便多了盆仙客来。很小的,但开许多花。带着黑色的塑料桶,已经被人撕烂了。或许正因此,便宜了母亲。这花一直养在我卧室的阳台。
我开始住的屋子是阴面,结婚时,母亲让出了她阳面的大屋子,自己搬到那个阴暗的角落里去了。仙客来喜阳,不能往阴地方放,只能摆在我这边。女人嫁过来那年冬,这花一直开着,一直开着。直到过完年。过完年,女人也就喜欢上了。不光母亲浇,她自己也浇。浇过夏,这株仙客来彻底蔫了。有好几天,不高兴。母亲舍不得丢,连盆,一块扔照壁后边的炭堆上。雨来雨淋,阳光却晒不着。到秋,突然看到蓬出一块绿来。呀呀,又活了。后来读了花书,才晓得,这花会夏眠。
现在呢,这花依在母亲的窗台上。而我们,却不在了。
现在,我的屋子里,也有了一株仙客来,女人养着。谁也不让碰。
二枚:君子兰
母亲早年种过一株君子兰,三四片叶,植株不大。摆在客厅地上,阳光晒进来,恰巧半边。母亲说,这花喜阴也喜阳。隔几天,她会把没晒着的半边换过来。这株花很沉默,从没多发出一片来,有新叶时,老叶必然会朽。母亲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家里阴气太重。
我们居住的房子是父亲单位的宿舍平房。很是接地气,耗子常常把洞从地下打进来,在墙角开出口子来。那口子上的水泥皮,不过几公分。我经常拿和稀的水泥灌耗洞,灌到灌不进去,拿把破菜刀的背抿住。家里没泥刀,母亲便想出这法子。这把破菜刀很管用,冬天,还要用来劈柴。夏天,母亲去房背后捡柴,也用它还割。刀并没有多少受损的地方,只是把上的木头朽掉了,不好拿捏,母亲缠些碎布条裹严实了,再拿电工胶布缠了两头,凑合着继续用。不过,这边修补好耗子洞,过些时日,又从那里掏开了。有时候,看不见。挪床,挪柜子,才发现,有些洞已经存在许多年了。
不光有耗子洞,还有泼鞋(hái)虫作害。就是潮虫。这种虫喜欢在背阴地不停地搜,那时候,我们的墙皮还不是这会儿的水泥包沙,而是泥墙。黄泥和着麦秸,外边再用黄泥抹光,上大白粉。这墙从外边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。可年代久了,就会掉皮。泼鞋虫就在这皮里生活,揭起皮,灰压压一群。那会儿,母亲经常边扫边抹泪,说,“这人家,什么时候是个头。”回头呢,我去地里铲了土,和泥,再把墙糊好。我娶女人前,这屋里到处都是补好的痕迹。娶女人时,问父亲要了些钱,把墙皮和地面都铲了,重新用水泥修整过。
没修整前的地,经常发湿。这屋子夏天其实很好住,凉阴阴。冬呢,却早早凉透。不过,母亲所谓的阴却不是指这个。而是指屋里有不净的东西。她总是怀疑,不然好端端的人家,怎么过成了这样。好端端的,父亲怎么就突然销声匿迹了呢。母亲本来不信神,后来,经常摆供,初一、十五。心很虔诚,但摆完了,又不得不大哭一场。
不知道是不是应了母亲所说。那些年,家里诸事不顺,就连花草也不肯长脸。这株君子兰从没有开花的迹象。大约是九年后,母亲终于耐不住了,要我把它丢出去。依然丢到了照壁后的炭堆上。到冬才拿回来。结果,腊月里,突然觉得里边鼓凸出什么,仔细一看,是蕊。这个变化令母亲欣喜若狂,她开始像以往那里爱惜起它来。每天没事就拿湿布子为它擦叶子,时不时用喷壶洒一番。就这样,这株君子兰长起了扁茎,在过年前开了花。很旺,很火红。邻居见了,都说挺喜气,都说我们那年一定会逢好运。
那年,我在塘沽寻见了父亲。
往后呢,君子兰隔几年开一次,长得逐渐茁壮。现在,它的子孙也在母亲的屋子里繁衍生息起来。而母亲也有了她自己的孙子,外孙女。
三枚:万年青
母亲曾经有株豆瓣青,高过了膝盖,有一抱那么大。叶子肥肥墩墩,很喜人。邻居过来,都眼羡。母亲却说,“有什么好,擦洗时候愁煞人。”她有个嗜好,没事时候,用干净的湿布子,把花叶一叶一叶擦去上边的浮土。管这营生叫“伺候”。这豆瓣青长到后来,密密的,也脆弱,擦一遍下来,好半天。一不小心,就碰断了叶子,流出眼泪似的黏稠汁液。所以,母亲便管它叫做“难伺候”,管那株不开花的君子兰叫“伺候也不顶用”。伺候的心烦了,就开始骂我们,“我成天伺候大祖宗小祖宗,什么时候是个完。”我们两个便悄悄的,耷拉着脑袋,像好几天没浇水的仙客来叶片。
这豆瓣青其实是乡里很常见的植物。豆瓣青、吊金钟、洋绣球、万年青。好像哪家哪户都养着几盆。却没个似母亲这般照顾,多摆在阳台上,任其黄叶染尘。顶多是花开败后,剪了枝,像洋绣球,不剪不好看。剪了,像落窝草鸡。毛乍着。母亲骂人好骂个“落窝草鸡”。比如我们的头发乱,没梳,她就会唠叨,“落窝草鸡似的,能不能像个人样?”赶紧过去,梳几下。
万年青是唯一不用剪。其实,乡里管豆瓣青也叫万年青。这两个大不同,之所以叫万年青大概是说,都是在看绿色吧。好像花都不显眼。后边这个万年青,其实是一种形似辣椒的植物,结一种灯笼似的圆果,初时青绿,老了便发红或黄。蛮喜庆的。不过,母亲却不喜欢,她总觉得,叫花不开花,算什么花。她养过万年青。只一两年,便给了人。我也不大喜欢,因为这果不能吃,听说还有毒。一个个光鲜地悬在那里,气煞个人。
除此,还有种植物也叫万年青,就是冬青。那会儿,不像现在,满大街都是。我还是在同学办公室门外初见。植株很高,高过脑门子。问同学是个啥,他也不晓得,去问了许多人,才告诉,是万年青。乘同学去找领导处理工作当儿,我赶紧做了偷香窃玉的营生,用小剪剪了一枝,装裤兜。回头,同学让坐,也没法坐。只说腰疼,喜欢站。这东西后来交给母亲,用罐头瓶泡些许时日,居然出了根。移栽在盆里,隔年就过了膝。再越一年,就窜及胸。问了高人,让做盆景。一听说,也是不开花的。母亲连夜送人。
豆瓣青却是母亲自己移来的。用一个叶瓣。她拿来时便有了根须。放盆里,慢慢地居然长成,亭亭玉立。母亲问过许多人,有人说开,有人说不开。但我家的,始终没见花骨朵。不过呢,这花有个好,新瓣绽开,也像开花。母亲便留下了。旁人有想要的,从没吐过口。大约是父亲有讯的当年,还是前一年秋,妹妹突然发现这花的顶端升出些团簇,淡绿的,似蕊。跟母亲说了。母亲很欣喜,说了句:“终于把你伺候出了光景。”更加精细地照料。过些时日,真的开成了花,红的,十字。一团团,像火焰。往后,年年开。
父亲回来后,租下村里的一个大院做办公。母亲其时养了许多花。橡皮树、滴水观音,都大得放不下。跟父亲商量,放那院。父亲应允后。我们欢丢丢寻了平车一概拉去。大冬儿,父亲却说,“没炭了。”去发煤。一冬没回来。我们也进不了那院。到春,一块儿没了。
以后,母亲再也不养万年青。
四枚:蒜苗
地方上冬天,临春时,家家户户,大都有栽蒜苗的习俗。概因秋后买的辫蒜到此时,多发生干瘪、朽坏故。却不是栽畦里,冬天的屋外,早已冻得僵硬,一锹下去,半分土也进不去。多用浅器具:盘碟、烂脸盆,瓦盆、木盒、罐头瓶。可以摆放在窗台上,也可以放厅间角落,能见着阳光,保证室温即可。
蒜须剥去外皮,露出白瓣。切掉根须部的、有朽坏、疮伤的、多弃用。这有点像挑飞行员时候,得把,剥脱个干净,让人家仔细验。我高中补习班时,有同学被挑去检验,回来都大光头,活脱两和尚。人家要验,头上凿没凿过窟窿?没窟窿才过,有过好了也不行。那会儿孩子大多玩劣,能够把玩的玩具多是土坷垃、石头之类。动不动就扔着飞,不小心便砸个血窟,医院拿药棉包扎后,过些时日便完好如初。再有,那时候,多上坡下坡,坡上多雨水冲刷的石头,一个后仰趴,好嘛,血窟。也有从土墙上往下跳,让墙下的高粱剪穿了小屁股的。至于弹弹弓、铁丝枪、铁链枪、钉枪、打架之类的,无不沾染着斑斑血泪。没窟窿?那是个怪。但人家就这么严,去了三个,只有一个愣没啥。到了部队,一验,怕高。得,搞地勤去吧,从没捞着飞行的机会。
蒜也如斯。且蒜还认品行。稍蔫点不怕,大蔫就不行。这跟单位要人一样,到哪,不都喜欢阳刚正气。内部朽坏最可怕,我小时候,让入团,首先得政治合格。再早先,父亲辈,还得根正苗红。蒜就是这样。稍有点差迟,“嘟,那厮还不退后。”
剥蒜是个细致营生,不能性急,抠破皮。小时候,家里的蒜多是妹妹拿来的。她早年被养在一个产蒜的村庄。秋假时候,多被奶妈接去。十来天,便混成个野孩子,脸黑皮肤粗。问说干吗了,答“辫蒜。”“辫了蒜干吗?”“卖钱。”回来时候,她会带一袋没法辫的蒜,我们都笑她,“这是你的工资。”这些蒜在冬,吃一部分,腌腊八蒜一些,还剩许多。快春前,母亲便嘱咐了,剥皮种。剥半天,妹妹便撅起了嘴,眼泪汪汪,辣的。说:“早知道这样,还不如不拿回来。”那时候,她还小,上小学,梳两绑鬏,就是朝天辫,胖乎乎的。吃奶时,奶妈奶水好,她也就身子底版硬。
栽蒜有土栽和水栽两种。水栽复杂些,得使唤针线,一瓣一瓣穿起来,搁器皿里,靠相互挤压立足。有点像,这二年的一个流行词:“抱团取暖”。我其实是很喜欢这个词的,经历过孤独的人,应该都喜欢,除非已经开始享受孤独。毕竟那二年,我们一家人都是相互支撑着才走到今天。立好足后,浇上清水,水不能太漫过尖。漫过久了,就淹死了。土栽就简单,将湿土搁器皿里,一瓣一瓣栽下去,不用管挤不挤,讲究些的,可以齐整些。毕竟齐整了,到哪都好看。这也应了那句:“人心齐泰山移。”
接下来的日子,就是母亲来照顾这些蒜了。那时候,我们都上学放学做作业,母亲担心耽误我们的学业。但我们仍旧喜欢趴在那里久久地盯着蒜尖看,什么时候出芽了。出芽了,人也是惊喜的。
到正月,蒜苗会长久一书高。下面葱白,上边葱绿。很好看的一道景。那会儿人家,大多有这道景。这景好看在哪里呢?蒜是辛辣的,辛辣的背后,永远是热乎乎的想望。
今日推介
诗集《天上的风》,借助当代诗歌表现形式,融蒙、藏草原历史与当下为一炉,以类史诗体系写作草原儿女马背上的爱情、雄健劲挺的生活,将此草原到彼草原的爱恨情仇,此时空与彼时空族人们的复活与挥手,以宏大的叙事手法,构成这本即充满激情,又满含无尽忧伤与回眸的马背情歌。诗集贯穿草原独有的神话、传说、民俗、风物等要素,尽展草原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特色。
长按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sh-chenfa.com/smzf/1677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