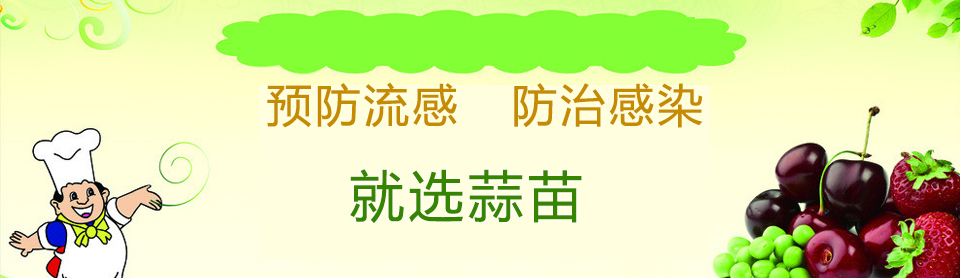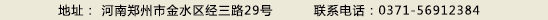那些年,武平人大山里挖蕨根的那些往事
点上方↑↑↑“武平生活”,获取武平全新资讯!
生活在武平山村的人对蕨子肯定很熟悉,它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,叶子跟其他的蕨类植物差不多。刚发出来的嫩茎,是难得的美味佳肴。挖新鲜蕨根,经过捶烂和落粉后即为蕨根粉,是一种天然的食品,蕨根粉中含有各种天然色素、矿物质和其他成分,特别是含有较多的类黄酮等抗氧化成分,口感很好。蕨根粉可再制成蕨根粉丝、蕨根叛等,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,可饱口福。
在老家时,每到春天到来,去山里采摘一些回来,把它跟大蒜苗炒在一起,不仅可口无比,而且很开胃,由于挖蕨根和落蕨根粉费工费时,己经被山里人遗忘。所以离开家乡多年了,对它的怀念也与日俱增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,当时粮食匮乏 秋冬季是生产队难得的空闲,为解决决饥饿是很急迫的问题,人们都忙着上山挖蕨根,野蕨菜,一岁一枯荣。秋冬季节,正是挖蕨根的黄金季节。山里人扛着锄头,三三两两朝长蕨根的大山进发了。
有一年冬天,我才十二三岁,母亲带上我去帮忙挖蕨。母亲为避免和别人发生争地盘的矛盾,刻意避开挖蕨根的人群,领着我独自来到一处叫老村里的山坳里,选择长势茂盛的一丛蕨,先用镰刀割去蕨的枝叶,然后扬起锄头用力挖开坚实的山土,就看到长在土层里拇指般大小的黑色蕨根。如果遇到土层浅且又松散的话,使劲一拉蕨根就出来了,否则就会拉断,还得再用锄头刨出来。有时挖蕨根,掘地三尺,要用出吃奶的气力,才能掘出。荆条一样、黑黑无毛、拇指般粗壮的老蕨根是上等的原料。春末夏初不会挖蕨根,因为蕨根鲜嫩,水叽叽,含淀粉少。
挖蕨根是个力气活,母亲一个劲默默不语地挖着,我则把蕨根上的泥土拍打干净,捡拢成堆。
午饭是早上带去的蕃薯干,渴了,就到山底下的小涧里喝上几口清澈透亮的山泉。冬日的白天时光短,残阳西沉之际,我们完结了一天的劳作,我和母亲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蕨根一步一晃吃力地向山下走去,我扛着锄头尾随其后,在崎岖不平蜿蜒曲折走的稚鸡山路上盖满了我们生活的脚印。那年月,我们硬是挺过来了。
从家里到挖蕨根的老村里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,而且山路崎岖,荆棘密布,稍不留心就会摔跤,就会被荆棘刺划得处处血印,火辣辣地痛。看见母亲因为肩膀上上百斤重的蕨根,再加上饥饿,其辛劳不难想见,没有这种生活体验的人,是难以想象的。
蕨根表面粗糙,带有须根,质地坚韧,还有点刺手,其内含有丰富的淀粉,充饥就是提取其淀粉来食用。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,生产方式落后的情况下从中弄出点淀粉,工序繁多,费时又费力。
回到家里,匆匆地把蕨根丢在河边,又匆匆地回到家里,匆匆地吃了点冷饭冷菜,然后又匆匆地来到河边洗蕨根,反反复复清洗,清除蕨根中依附着的泥巴、沙子、杂质。洗好蕨根后,找一块平坦的大石板,用来捶蕨,捶蕨根比挖蕨根更辛苦。洗完后,要把蕨根翻来覆去的捶很多遍,直到呈粉末状。捶蕨根辛苦,苦就苦在要用很大的木槌,大概有二十多斤重,因此,你在捶的过程中,你会感觉到木槌越来越重,没有多久,你就会累得气喘吁吁地。捶蕨时蕨浆水汁会四处飞溅,溢满全身,捶蕨根非常讲究效率,所以,挖掘根的人会相互帮着捶,这样就更快,他们一高一低地木槌声,虽然单调,但也像一曲动听的农家曲。
蕨根捶好之后,接下就是落蕨粉。落蕨粉的工具就是两个木桶楻和谷箩,木桶楻是一大一小,大的是打稻谷用的禾桶,小的桶楻底下连着竹筒,小桶楻在高处,大桶在低处,而且用一根大的竹筒把它们连起来。箩匡里用蕨根渣做过滤器,大桶上的箩匡也要用棕衣或旧蚊帐布做过滤器。这个过程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,所以,过滤完之后,往往是夜幕降临了,母亲这个时候也累得筋疲力尽了。
第二天再过滤的时候,把水放干,留在底部的就是蕨根淀粉,每天大概都有十斤左右。母亲每次都会小心翼翼地用锅铲把它装到从家里带来小木桶里,生怕有一滴掉在地上,万一有那么一点掉在了地上,他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弄回到桶里——那毕竟是汗水、辛劳甚至是心血的结晶啊!
24小时之后,大木桶的水清澈起来,可见沉淀的蕨淀粉,排干水,铲起湿漉漉蕨淀粉,放到另一个桶里。再加水到桶里,搅拌,在一块纱布上过滤,循环往复,直到滤干净杂质为止。最后,将湿蕨淀粉糊成一坨,放置到簸箕里晒。晒干,蕨淀粉就大功告成了。产品历经十多年都不会变质。
这些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,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可是,母亲做蕨根粄的情景还粒粒在目,蕨根粄的独有的芳香至今还在口头荡漾。在那个充满艰辛和无奈的年代,母亲正是靠蕨根粉撑起了我们的梦想,没有他(它),也许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文:李志祥图片来源网络
广告、投稿、爆料请加
中科白癜风让白斑告别
中科白癜风医院健康庆双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sh-chenfa.com/smjz/12373.html